| 东西交流论谈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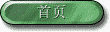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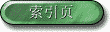
|
朝鲜西学的历史意义
一 序 言
所谓文化就是人们通过自愿完成的生存斗争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有不同个性的每个人完成生存的活动不但具有人的同一性和同质性,而且也表现出异质性和多样性。同样,特定民族的文化,在其文化产生的各种条件之差异中表现出文化的“种差”,即生存完成区域都带有一定的同一性和同质性,用来形成文化封闭区的“种差”,我们把表现出这种区域种差的一个个文化规定为“文化体”。 各种文化体在其限区自然环境中通过区域成员的自发性生存斗争而形成原始种差(特性)。但是,各种文化体一方面超出或克服其文化内所含有的本身制约,另一方面与其它文化体进行“存在论的对话”来摸索高水平文化体的发展。换句话说,不仅要“接触”其它文化,而且要接受其它文化的“挑战”,对此还会进行“应战”或“协助应战”,最后又会经历“接变”的新文化过程。各种文化体的互相接触、互相联系和互相协助,这是人的生存完成形式的一种“形态显露”,依靠“存在论的对话”来进行文化交流,正是文化本质的显露。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本质“外形性形态显露”和随之而来的“外面性接变形态”而不断发展起来的。 如果把文化人类学的逻辑转换到历史发展的逻辑来看,那就可以把能推动历史发展的历史动力(historical energy)的内因论(亦称内在论)和外因论(亦称传播论)归结为不可缺少的因素。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演变,这种演变是为其民族社会中酿成的内动力(internal energy)所推动的。另一方面,历史演变也可以通过外部刺激或冲击来进行,即在民族社会外面也可以寻找促进历史变化的变数因素。变化的历史主体是孕育并萌芽成长在民族社会内部的历史动力,而它以发动或推动为转机,与民族社会传统价值体系不同的、基于异质性价值体系的刺激或冲击作为“客体”也起作用。 传统社会如果面临含有新价值的“异质性历史冲击”,必然为传统社会人们发生历史的反应(historical response)。这种反应以拒绝和接受两种形态出现。对于异质性挑战的反应会产生接变,历史随即进入新局面,历史发展总是通过这种新局面而得到进展。 历史证明,我们民族的原始文化起步于同北方民族萨满文化有关的“类型”,后来接触汉族社会的汉字和儒学、儒教以及佛教等外部异质文化,通过与之相对立的历史展开而接受并消化异质文化,使韩国人的传统文化步入轨道,从而促进了韩国历史的发展。汉字、儒学只是汉民族的产物,而不是我们的文字或我们的学问。但是,依靠我们民族的文化能力吸收为我们的文字或我们的学问,于是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与此同时,去开导未来意识,使现实生活得以发生变化。作为我们文化的基干因素而在我们历史上占有地位的佛教,本来是从印度人的思索或思维中产生的一种宗教。我们民族通过中国而接受佛教为“汉字佛教”,但为着了解和吸收佛教,有很多渡唐求法僧前往中国研究佛教学,甚至还有渡天竺求法僧去了佛教故乡印度。另外,国内学僧、大德们的佛教研究得到了发展,以佛教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在我们民族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消化和溶化。由于这种反应作用的发展,外来宗教——佛教变成我们的佛教,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文化。这样,外部文化的刺激和历史冲击给我们民族培养了民族的历史动力,推动了我们文化的发展。不消说,这种变化和发展之所以得到推动,是因为与之调和得巧妙,生产上能够接受的内部条件已经成熟,即内在动力更加牢固。 朝鲜王朝后期社会是个基于儒佛传统价值的传统文化世界,它又受到另外一种新的异质价值体系的历史冲击,那就是立足于基督教价值的西欧文化体系即“西学”的冲击。 自宣祖朝以来,从明清传入朝鲜的“西学”正是一种欧洲基督教文化体系,它成为促进朝鲜社会变化的历史变数。
二 “西学”同朝鲜王朝后期知识分子的接触
“西学”一词,原意为中国明末清初基于基督教价值意识的有关西洋及西洋文化的学问,开始流传于知识分子中间。 明末清初,有关西洋的书籍均由耶稣会士译成汉文,称之为“汉译西学书”,或称为“汉文西学书”。这是因为耶稣会士自己在他们所著有关西洋的书籍中称西洋学问为“西学”,后来中国学者亦称之为“西学”。 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在明都北京落下脚,始创中国天主教会,同时把天文、历法等西欧学问技能开始使用在明皇室,从此四年后的1605年,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us Vagnoni,后改名为王丰肃)定居南京,并主管南京天主教会,发表汉译西学书共达十五种,其中有《西学治平》、《民治西学》、《修身西学》、《西学齐家》等书。《西学治平》共有十一章,为西洋政治学书,其续编为《民治西学》。《修身西学》由十一卷组成,为西洋伦理学书。此外,《西学齐家》亦属西洋伦理学书。艾儒略(Julius Aleni)神父比高一志神父来华晚一些,1613年他作为传教神父来到中国,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开展传教活动,而且发表《职方外纪》等三十多种西学书。其中有1623年在杭州写成的《西学凡》。《西学凡》介绍了西洋的大学教育及教育过程,是一部有关西洋教育及学术的概览。他阐明当时西洋高等教育及学术生活毕竟以基督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在中国从事文化主义、迎合主义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所介绍的西洋学问为“西学”。不仅是耶稣会士而且当时同耶稣会士关系深厚的硕学高儒也曾使用过“西学”一词。 “西学”是所谓地理发现以后伸向东方世界的欧洲历史动力对着东北亚儒佛传统文化体施加西洋价值体系的一种挑战,即东北亚知识分子面对基督教文明冲击以“学问应战”形态来进行历史反应的“显露态”。那是地理发现以后,从事掠夺性冒险贸易的商人和从事政治性殖民活动的侵略尖兵以及紧跟着他们欲在异教世界传播基督教福音的传教士从文化宗教方面扩大欧洲的以“历史挑战”形态来进行的历史冲击。耶稣会作为东洋传教尖兵按照东洋巡察使范礼安(Valingano)的适应主义传教方针,同当地社会及当地文明进行了妥协性的传教活动,而且还实行了迎合传统社会及传统文化的传教政策。 根据这种传教策略,耶稣会传教圣徒们向中国介绍基督教信仰及欧洲科学技术,不仅将西洋文化传播到东洋社会而且还引导传统知识分子能够了解西洋、接触西洋文明。为此,他们刻苦耐劳,将西洋典籍译成汉文而介绍到中国社会。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异教世界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也包含着文化意识,就是把西洋文化移植到异质文化世界——儒教传统社会。由此可见,留华耶稣会士的文化主义、补儒主义传教活动,在文化上也引人注目。 有关西洋学问的书籍均由他们所编,我们称之为“汉译西学书”。“西学”就是明末清初利用“西洋文化”及“汉译西学书”以中国大陆北京为中心而掀起的新学风。 《天主圣教实录》是一部最早的汉译西学书,于1584年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神父所撰。后来,由利玛窦神父编撰并于1603年刊行的《天主实录》乃是第二次出版的汉译西学书。利玛窦曾经编撰将近二十卷西学书,而且用汉文译制成世界地图《万国舆图》。此后,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所属传教圣徒们(其国籍极为复杂,有意大利、德国、法国、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波兰等等)继承罗明坚以及利玛窦的传统而致力于写作活动,以便从学问上介绍西洋文明。 在明末清初同耶稣会员有关的汉译西学书当中,或有耶稣会员直接用汉文编写的,或有他们口传后由中国协助者编写的,还有他们写稿后借助中国人加以润色的。《天主实义》和《西学凡》分别由利玛窦和艾儒略编撰;《几何原本》先由利玛窦讲述,后由明末硕学名臣徐光启记述;《灵言蠡勺》由毕方济(Sambiasi)口传,徐光启笔录。 利类思(Buglio)在自序中关于他的汉译西学书《超性学要》称,“经我翻译借助中国人加以润色而刊行”。明清时期中国人的“笔录”也好,“润色”也好,译成汉文出版的毕竟是耶稣会西洋圣徒。这些耶稣会士在翻译西学书时,给予协助的除了被人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以外,还有冯应京、李天经、王徵、韩霖、段衮、瞿式相等硕学者。 曾参加过汉译西学书的耶稣会员们因为能够自由阅读中国古典及古书,所以连细腻的中国古典都非常熟悉,岂止如此,他们还深入研究中国文物、制度和风俗,以便自由自在地运用在著作中,因而博得了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赞扬。他们的学问活动和写作活动为正教和西洋文物在中国的传播而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清时期,耶稣会士们滞留在北京东部、南部及北部三座天主堂从事传教活动,各天主堂均备置丰富的图书馆藏书。正因为图书馆所藏西方书籍十分丰富,所以西洋圣徒们依靠学问热情和传教欲望而能够编撰许多汉译西学书。 当然,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的各传教团体中,把西洋书籍译成汉文出版的不只是耶稣会一个团体。比耶稣会晚一些,即从1631年起在中国从事传教的圣多明我会(Dominican)、从1633年起开始的圣方济各会(Franciscan)、1680年活动于中国的圣奥斯定会(Augustin)、1684年进入的巴黎外邦传教会(Société de Missions-Etrangéres de Paris)等各种传教团体所属圣徒们也曾进行过写作活动。众所周知,耶稣会士的写作活动最为活跃,他们所推行的传教方针就是一面采取补儒论立场一面紧密结合中国社会。 自从耶稣会在葡萄牙向东洋进军的根据地澳门建立东洋传教据点而后向顽强的异教世界——中国内地进军的1583年(罗明坚神父及利玛窦神父入住肇庆)起,一直到1773年(清朝乾隆38年)被教皇克莱孟(Clemence)十四世勒令解散留华耶稣会为止,这一百九十多年期间由耶稣会亲手译成汉文的书籍共达五百多种。这些众多书籍大致可分为西洋科学技术(即“器”方面)和西洋伦理宗教(即“理”方面)。具体地可分为西洋中世纪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技术、学问及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西洋社会伦理与宗教等方面。这些汉译西学书在明清时期不仅引起先进知识分子学问上的特别关心,而且受到那些努力研究天文历法的技术官僚以及关心异质文化的先觉学人的关注,他们从农业社会“皇帝之学”的需要出发都十分重视这些著作。进而提供这些书籍的耶稣会所属西洋圣徒们被聘请为皇室御用学者或技术人员,积极地把科学技术传播到北京。由于这种努力和皇室的关怀,明清时期西学得到发展,终于在明末清初的北京一角出现了所谓“清欧文明”。 明清时期移植于北京一角并已汉化的欧洲文化即“清欧文明”通过赴京朝鲜使者而源源不绝地流入汉字文化圈范围内的政治封锁世界——朝鲜王国。政治使者承担刚刚汉化的西欧文明的“文化导管”作用,以最初汉译西学书著称的《天主实义》就借着这种作用,于1603年译成汉文出版后还不到十年便传入朝鲜社会。因此,从17世纪初开始就有很多知识分子热心阅读这本书。另一方面,通过李光庭所传来的汉译世界地图、郑斗源所引进的西洋文物、照显世子与汤若望神父之间的交流等几个实例,也可以知道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常年累月不断地流入朝鲜王朝后期社会。与此同时,许多技术官僚及在野知识分子出自实用上的需要和学问上的好奇心而逐渐接近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 同西洋及西欧文明的接触并非借助于漂流洋人,而是通过留京朝鲜使者和北京四座天主堂以及耶稣会圣徒所辖天文历法机关——钦天监才实现的。这种接触的韩方主角乃是农业社会“帝王之学”——天文历法方面技术官僚和格外关心大陆文明的北学少壮派学者。后来,他们以搬入国内的汉译西学书为媒介,依靠国内在野少壮派学者所编书籍而孜孜不倦地进行了研究活动。因此,接触场所首先是北京,然后就是国内在野知识分子的书房。前者是同留京洋人的直接接触,后者是通过国内汉译西学书而进行的间接接触。
三 “朝鲜西学”始末
从17世纪初开始不断传入朝鲜王国的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随着天长日久,其种类就更加丰富了,其数量也更加增多了。先进知识分子或出自实用上的需要或出自好奇心而开始阅读和研究当时已经传入国内的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一个多世纪后,实学者星湖李瀷不止单纯的好奇心,而出自非凡的学问关心,浏览并研究了西学资料。他研究西学的热情由其弟子以及所谓“星湖学派”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湛轩洪大容以后,北学派学者亦赴清都北京拜访请教西洋人,从学问上致力于西学研究。于是,“朝鲜西学”的学问世界终于启幕。 星湖李瀷的高徒顺庵安定福是一位有名的实学史家,他关于18世纪中叶汉译西学书的流传情况有如下记述:“宣祖末年以来,汉译西学书流入我国,名官儒生无所不闻,常时备置于书斋,视如诸子百家著作或道佛之书。”可见,当时汉译西学书流传得非常广泛。茶山丁若镛对年轻知识分子笃学汉译西学书的情形说成是“年青时之流行风气”。显然这是京乡地区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学问活动,但可以看作对儒教传统社会也能促进变化的一种历史冲击。 “朝鲜西学”是在朝鲜王朝后期儒教传统社会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利用汉译西学书及西洋文物而进行的一种学问活动,有别于利用“泰西新书”进行学问活动的洋学。所谓“泰西新书”就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所编的西洋研究书,目的在于了解西洋并把握对方,借以克服危机状况。纯祖朝以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易言》等泰西新书传入朝鲜,其编著者均为中国人。因为这些书是已经采用西洋“近代”的洋学书,所以有别于西洋耶稣会士利用传教性教材汉译西学书而进行的文化活动。而且,其内容含有一种西洋“中世纪”学问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因而又区别于中国人利用洋务书籍而进行的学问活动。 “朝鲜西学”大致经过了四个发展阶段,最终面临窒息。 ①西学接触时期:1603—1730年代。利玛窦经明朝神宗皇帝特许在北京落脚之后,参预钦天监工作并开始传教活动,他按照文化主义、补修主义传教方针写出了许多汉译西学书。留京朝鲜使者或者从农业社会官僚书籍的需要,或者被好奇心所驱使而拜访钦天监和四座天主堂,以接触开明的西学,同时把西学资料(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搬送到母国朝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但其种类增加而且其数量也增多,流入国内的以往西学资料就成为一些好事者的接触对象。这时期也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偶尔发表短篇论评或消息,但都没有经过学问考察。只不过是如同李睟光的短评性记载,或如同李荣俊的职业性探问,或如同李颐明的好奇性记录而已。 这时期,同中国西学的首次接触是通过留京朝鲜使者与留京耶稣会士之间的一面之交而实现的,第二次接触则是通过朝鲜王朝后期儒教知识分子直接从耶稣会士取得的资料或搜集从北京输入朝鲜的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而实现的。 ②西学探求时期:随着国内汉译西学书的种类丰富和数量增加,接近汉译西学书的好事者也就增多起来。这些书籍,有一部分先抄写后再流传,也有一部分互相借阅传读。接近这些西学书的人物当中,既有入燕官僚或技术官僚,又有众多儒教知识分子。 对汉译西学书的阅读以及同留京耶稣会士的接触,终于发展到求学欲上的探求,也就是说,当做问题去浏览汉译西学书并且沟通耶稣会士。这种风气从星湖李瀷及湛轩洪大容开始形成,时为18世纪中叶。李瀷以强烈的西学热情来搜集并读破当时正在流传的汉译西学书。他不仅证明并领会其真髓而后加以记录,而且同周围人士进行研讨,还劝告诸弟子研究西学。从此,探求西学的幅度空前扩大,程度也一日比一日深入,使朝鲜西学得以迅速发展。李瀷为星湖学派学者,掀起了西学的新飞跃,而西学则依着他们得到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朝鲜西学通过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揭开帷幕。他们之中,顺庵安鼎福、河滨慎后聃等人对西学采取了排斥的态度,与此相反,鹿庵权哲身、旷庵李檗、茶山丁若镛等人却采取了接受的态度。 湛轩洪大容亲自到北京以科技方面的敏锐眼光来探求西学。接着,燕岩朴趾源、雅亭李德懋、楚亭朴齐家等所谓北学派实学者前往北京同耶稣会士或清朝硕学进行学问交流,借以提高北学意识,更加致力于西学研究。 西学探求时期,朝鲜西学的学问资料是明清以来的西洋文物及汉译西学书,研究场所则是国内及北京。北学派也曾经在北京获得西学资料,回国后以炽烈的求学欲来专心研究西学。无论是以李瀷为首的星湖学派学者还是以洪大容为首的北学派学者都提高了朝鲜西学的学问性。 朝鲜西学是一种异质价值体系,尽管它具有足以催促传统儒学世界变化的可能性,但由于历史所限,其研究者却局限于极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其学问活动亦存在异学的趋向。 ③西学实践时期:正祖年代(1777—1800年),即18世纪后期定为西学实践时期。从正祖时代起,以在野南人少壮学者为中心,将西学所提出的问题付诸实践。 西学的“器”方面属于西洋科学技术,早就被人们运用,比如孝宗时期曾采用过汤若望的时宪历,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到1782年(正祖六年)遂在书云观制成千岁历;又如营建水原城时,丁若镛对西洋“起重架说”加以研究,遂制成滑车及滑轮,用来减省建筑费用。但是,作为“器”方面的科学技术,在接受和实践上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反之,作为“理”方面的宗教伦理被接受之后却奉行天主教信仰,给朝鲜王朝后期社会以巨大的冲击。 一些在野南人少壮学者从学问上的关心出发一直把天主信仰及基督教伦理看做天主学(天学)来加以研究,并企图使之贯彻到现实生活中去。即从来沉浸在儒学教育的西学研究者,或者个别地或者集体地(例如天真庵走鱼寺讲学会)自行研究天主学,终于劝醒了补儒论的天主信仰。1784年(正祖八年),他们利用李承薰领洗回国的机会,以李檗、权日身等为首定期举行信仰集会,终于创立了韩国天主教会。天主教信仰实践运动的参加者只不过少数而已,但他们却是早期天主教会创始人。他们不顾乙巳秋曹摘发事件、丁未洋会事件、辛亥珍山事件等种种压迫,通过个人传教活动和用教理书来进行的文书传教活动以及天主歌词等各种传教手段,一边扩大天主教势力,一边开展圣徒迎接运动,最终把周文谟神父从清国迎接到朝鲜来。另一方面,因焚主废祭问题而发生辛亥珍山事件之后,趁此机会就推毁补儒论天主信仰界限而加强了天主教信仰奉行。其结果,到了正祖王朝末期,教徒已达三千多人。 这些天主教徒接受基督教信仰以树立起基督教价值观,而且还接受了十戒基督教伦理生活实践价值。从这一点上看来,奉行天主教信仰就是西学中“理”方面的实践性接受,同时也是基督教价值观的接受。 ④西学伏流时期:1801年(纯祖一年)的辛酉迫害是儒教封建统治势力直对着天主教(天主学)历史冲击而展开的一种抨击。这就是要维护性理学价值体系的儒教社会势力的反冲作用。当然,辛酉迫害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乙巳秋曹摘发事件、丁未洋会事件、辛亥珍山事件等,诸如此类,都是对新生西学“理”方面实践组织——天主教的镇压和迫害。此外,反对强力镇压的性理学斥邪上疏犹如滂沱大雨,也属事实。可是,当时的执政者正祖王却强调正学(性理学)的振兴,过于看轻事实,认为邪学(天主教)将自生自灭,正学振兴则邪学终将自灭。纯祖即位后,僻派的党争日甚一日,遂颁布斥邪纶音,在全国范围大力迫害天主教。从此开始的天主教迫害不仅是强力镇压,甚至还企图拔本塞源,按照“天主教信仰及伦理→天学→西学之‘理’方面→西学”的次序,不加区别地扩大迫害对象,致使西学全面被封禁。 由于迫害者不能分辨出西学中理(宗教伦理方面)与器(科学、技术)的区别而进行强力镇压,对朝鲜王朝后期社会近代化应有贡献的西洋科学技术全面被拒绝,这是一种历史错误。即使排斥或抵制基督教宗教伦理,也应当为物质文明发展而采用先进科学技术,这是当时的历史义务。可惜,这些都被回避或拒绝,朝鲜王国仍固守传统而停滞不前,遂耽误了向近代化的步伐。 从纯祖到宪宗的过渡时期,由于从外船入侵中受到刺激,从文化斥邪发展到政治危机,其程度大幅增长,政府高压政策亦更为强硬化,致使西学频于危境。尽管情况如此严重,但在五州李圭景、惠岗崔汉绮、秋史金正喜等人的书房内却仍然存在着微弱的西学气氛。 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萌动起来的对内外开放意识被窒息在摇篮内,鉴于世界史的潮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不顾强力镇压而培养出将近一万人的教徒,竟自坚守信仰,发展天主教会,这毕竟还是接受西学后所取得的唯一成就。总之,天主教对于前近代朝鲜社会无形中起到了浸润作用。
四 “接变”的萌芽
自17世纪初起在异国土地北京同“清欧文明”的接触,此后不断引进的西洋文物和汉译西学书以及对其认真细致的研究,始于18世纪中叶“朝鲜西学”学问活动,是一种朝鲜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对着西学的西洋冲击加以研究而后交叉进行接受和抵制的历史反应的具体化。这种“挑战”和“应战”的历史过程,究竟对儒教传统社会——朝鲜王朝后期社会产生了哪些“接变”的可能性呢?在哪些程度上为后世形成了推动变化及发展的历史基础呢? 简单说来就是近代思想萌芽的西学的觉醒正在提高。规定近代思想基调为对准于理性、自由及民族的价值体系时,领先于它的思想萌芽便是针对中世纪普遍、先验及闭锁的以个别、合理及开放为基础的启蒙。 在儒教朝鲜中世纪社会中,接近这种近代思想的启蒙(萌芽意识)正是通过西学的学问活动才实现的。开初,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接近西学,后来进一步专心学问研究以开创“朝鲜西学”道路的星湖学派以及能够获得留京良机的北学论者,依靠在“朝鲜西学”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使朝鲜王朝后期儒教传统社会内部得以生长近代思想的萌芽意识(启蒙)。 其萌芽意识的征候出现在各方面。本文拟对这种征候从世界观变化的个别意识和有所了解实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意识以及遵从天主教信仰实践的人间意识等问题加以分析,并当作规定“朝鲜西学”实学性的基础资料。 (一)向近代世界观接近:华夷论世界观的动摇 据片断资料所载,近代欧洲是通过中宗时期赴京朝鲜使者李硕所著《见闻别单》才传扬到朝鲜社会的。从此,西洋“佛朗机国”的存在才传开了。此后,通过李睟光所评论的汉译西学书中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朝鲜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西洋并非一种白日梦幻,而是客观存在。另外,仁宗、孝宗时期的漂流洋人尽管在文化上没有对朝鲜社会做出特殊的贡献,但使朝鲜人真正感受到西洋世界的存在。 17世纪以前的朝鲜对西洋的认识,不过是地理上《山海经》之类的奇谈,或者是反映中华世界观的世界地图——《混一疆理历代国之图》。这是朝鲜知识分子(儒学者)区别“华”、“夷”的所谓“尊华”、“卑夷”的华夷思想,是同“天圆地方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7世纪引进的各种汉文世界地图以及《职方外纪》或《坤舆图说》之类的汉文世界地理书推动了那种前近代中华中心世界观的变革。特别是《职方外纪》使传统社会得以初步认识世界地理及西洋文化。 李瀷因为曾通读过《职方外纪》,所以能够阐明《职方外纪跋》。他不仅接受了《外纪》及《西洋舆地图》所述的世界人文地理知识以及有关自然现实的西洋自然地理知识,而且还接受了“地球说”,克服了所谓“天圆地方”的传统说法。他举出哥伦布及麦哲仑绕世界一周之例来真正理解到“地球说”,还引用地心论来说明人类居住在地球表面上却不掉落到空间的现象,这可谓是通解“地球引力说”的结果。由李瀷所认识的“地圆”,到洪大容发展为“地转”。洪大容已经懂得地圆地转,其著《毉山问答》(《湛轩集》内集·补遗,卷四)称:
且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例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覆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
由此可见,他否定了“正界”即中国这一固定的绝对的中华中心世界观,认为“正界”不过是相对概念,世界万方均是正界,揭示了可谓革命的世界观。不仅如此,连传统中国中心世界观的基础思想——华夷之分、内外之分等春秋大义本分论都为他所否定。他在《毉山问答》中运用虚子与实翁之间的对话形式作了如下论述。
虚子曰:孔子作春秋,内中国而外四夷之分。…… 实翁曰:……自天视之,岂有内外之分哉?是以各亲其人,各尊其君,各守其国,各安其俗,华夷一也。……四夷侵疆中国,谓之寇;中国黩武四夷,谓之贼。相寇相贼,其义一也。……虽然,使孔子浮于海居,九夷用夏变夷,兴周道于域外,则内外之分,尊攘之义,自当有域外春秋。此孔子所以为圣人也。”
据此,不能不感到,他不仅接受单纯的西洋地理知识,而且从根本上就否定传统社会金科玉条——中华中心儒教世界观,而转回到“万邦均是”的近代世界观。通过西学而得到的科学天文地理新知识竟然提出了敢于否认“内外之分”、“华夷之分”等春秋大义的思想。中华中心世界观和以小中华自居的落后文化意识从此向科学的世界观飞跃起来。在此我们可以感到能寻找所谓脱离“汉”的个别意识、自主的国家意识、开放的文化生活等近代思想萌芽的意识转变。 (二)倾向合理实用科学:对西欧科学技术的认识 仁祖时期的遣京陈奏使郑斗源进入北京之后,让译官李荣俊学会天文推算法,又让别牌将郑李吉掌握红夷炮操作技术,随即归国,这是儒教传统社会朝鲜王国要利用西欧科学技术文明的开端。引进西洋科学技术来运用到朝鲜社会的先例乃是孝宗王四年所采用的“时宪历”。在中国颁布西洋历法“时宪历”来代替从前大统历法及回回历法不到八年的1653年,朝鲜王国亦抛弃自古以来《七政算外篇》而采用“时宪历”,其敏捷的反应令人惊讶。这应当归功于孝宗时期的观象监提调金■。李颐明是肃宗时期老论四大臣之一,他曾在赴京之前熟读过《治历缘起》、《天文略》、《同文算指》等汉译西欧天文书,前往北京逗留期间,他曾函请蘇霖(Saurez)及戴进贤(Koe- gler)神父指教,还得到面谈机会而向他们尖锐地提出了立足于“西洋天文学十二重说”的天体结构运行以及历算法等问题。 李瀷对西学“器”方面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曾感到遗憾,因没有西洋望远镜而无法直接观测西欧天文书里的“十二重天”。李瀷从实利的博学精神出发,积极谋求克服现实矛盾的学问方法,而且还通读当时流传于世的三十多种汉译西学书,致力了解西欧科学技术。李瀷不愧为农业社会读书人,通过西学关于宇宙结构、天文体系、历算推步等方面的科学认识,领会其先进性,还曾谈论过基于学理的利用方法。他关于西洋历法的正确性竟敢称道:“圣人重生,必从之矣。”关于天文推步的优秀性则称道,“中国未曾有过”。他研究《几何原本》之后,对其中数学能克服学理者的“浮气”,能熟习“正气”,能增强学事者的“定法”,能造成“巧思”等主张表示赞同,称说“每试之果验”,因而可谓他合理地接受了数学教育中为形式所熏陶的教育价值。他又通读汉译水利书——《泰西水法》,认识到西洋水利技术优点,而且还提出了西洋水利设施采用方案。 李瀷的科学观察,不是只停留在自然界或产业方面,而是涉及到生理机能和医学。李瀷通过西学书《主制群徵》而能够科学地接受西洋医药知识,甚至还把这些知识运用到西洋画欣赏方法上。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李瀷对西洋科学技术的认识,其程度固然低下,但他冲破儒教传统科学技术权威而发挥尖锐的批判精神和坚定的证实精神来认识新的科学技术,就这一点而言,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科学思考和合理见解就更加浓厚起来。 洪大容的西学热情很高,他向曾徘徊在“天圆地方”儒教宇宙观的朝鲜学界提出过地动说,他作为水利方面的专家曾利用西洋数学发表了叫做《筹解需用》的算学书,他在自己的住宅内建造笼水阁,又设置浑天仪和自鸣钟,用来埋头研究天文、时制,他为寻找西学丛书《天学初函》而奋斗了十年之久。他的科学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对西洋科学技术的优秀性和正确性赞叹不已,写道:
今泰西之法,本之以算数,参之以仪器,度万形,窥万象。凡天下远近、高深、巨细、轻重,举集目前,如指诸掌。则谓汉唐所未有者,非妄也。(《湛轩日记》,卷1,《刘鲍问答》)
35岁时,洪大容以使者身份前往北京与清国考据学者潘庭筠、严诚、陆飞等人一起谈论学问,曾三次拜访过天主堂,而且还同西洋圣徒关于西洋天文、历法、数学、音乐、宗教等方面用笔谈交换了意见。他对清欧文明予以特别关心,遂评论科学技术“非末技而乃精神之极致”,力主打破过去错误的传统科技观。他是具有为取用真实(科学)而不顾一切的坚强的合理精神。他对西洋科学的认识以及对技术的信赖恰恰形成了那种合理态度。
苟利于民而厚于国,虽其法之或出于夷狄,固将取而则之。(《燕告集》,卷12,《别集·热河日记·驲讯随笔》)
朴趾源如此强烈地呼喊“北学”,这种生气勃勃的合理精神也引人注目。他曾经进入北京而从学问上努力接触清儒,以增强实学意识,还交往天主堂的西洋圣徒,深入了解西洋科学技术,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北学”意识。 北学派的另一个巨匠朴齐家认识到西洋科学的优秀性,应和西洋传教圣徒的主张,积极提倡谋求国家实利。中国钦天监所属西洋圣徒通晓“利用厚生之法”,因此朴齐家主张拜他们为师,学习天文、历学、农桑、医药、建筑、采矿、造船等科学技术。他一边提出上述方案一边还揭发道:
虽其为教,笃信堂狱,与佛无间,然厚生之具,则又佛之所无也。取其十而禁其一,计之得者也。但恐待之失宜,招之不来耳。(《贞蕤集·北学议》,附《丙午所怀》)
从当时社会风气或文化动向来看,这的确是惊人的技术引进论,是对西洋科学的主张。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主张,首先是因为北学派的实学意识十分明确,其次是因为合理地认识到西学的科学技术。 丁若镛被人誉为实学集大成者,1797年他向正祖呈上《自辟文》,陈述自己年轻时一度染上西学的情况。书中载,之所以接近西学是因为西学的“天文历象之说”、“农政水利之器”及“测量推验之法”对他有极大的吸引力,即他被西学的科学技术优秀性所迷住。丁若镛钻研先行儒学家的儒学思想,领会以天命为基础的天道政治思想精义,遂做出茶山经学成果。在腐败不堪的朝鲜王朝后期,他为着实现为民造福的王道政治,专心摸索国家机构的整顿方法,致力于官僚的道义刷新。为了“国富民裕”,他强烈主张以“利用厚生之法”来采用北学(接受汉译西洋科学及技术的清国先进文明)。这种文化意识,由于他自己一度染上天主教并且相当了解西洋科学技术而更加明确。 从丁若镛的技艺论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的逻辑是十分合理而科学的。
天之于禽兽也,予之爪,予之角,予之硬蹄利齿,予之毒,使各得以获其所欲,而御其所患。于人也,则裸然柔脆,若不可以济其生者。岂天厚于所贱之而薄于所贵之哉?以其有知虑巧思,使之习为技艺以自给也。而智虑之所推运有限,巧思之所穿凿有渐,故虽圣人,不能当千万人之所共议,虽圣人,不能一朝而尽其美。故人弥聚则其技艺弥精,世弥降则其技艺弥工,此势之所不得不然者也。(《与犹堂全集》,第1集,诗文集,<技艺论>)
他认为人的特性在于以智慧和思考为基础的“技艺”之中,而传统儒家则把人与动物的区别放在以三纲五伦为基础的道德标准之上,因而两者的发端截然不同,别具一格。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技艺依靠多数集体努力的视角性积蓄而发展,这无疑是认识到历史发展概念的一种开端。我们从丁若镛的这种进步而合理的技艺论中,不仅可以体会到他的科学态度和利用厚生的实用精神,而且还可以体会到他赖于科学工夫的思想基础。他被进步的“天文历象之说”、“农政水利之器”、“测量推验之法”所吸引而醉心于西学,主张设置能承担起实用科学的国家机构“利用监”,钻研西洋力学技术书籍《奇器图说》而拟订出《起重架图说》,同时在水原城建筑工程时,利用滑车及滑轮来减少了大批劳动力,节省了四万缗费用。 如上所述,西学研究者对西洋科学技术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实用的开放态度以及立足于阴阳五行的理学性自然哲学(自然结构的基本原理)为深受西学影响的人士所重新检验,这是值得重视的事情。 《周易》阴阳及《书经》五行通过汉代今文经学家而变成儒教自然哲学基本理念。到了宋代,周敦颐和朱熹进一步加强性理学伦理,从而变成性理学的自然哲学,它被接受到朝鲜儒学而成为圣典。在西学中,不是以“理”和“气”来说明存在,而是分成“理”和“物”来加以说明,“物”具有自立性,而“理”则具有依赖性,从而否定“理”的实体性。西学提出了与儒家的五行说(即把水、火、金、木、土看做气的构成因素)全然不同的四行说,即认为“物”的构成因素是“气”和“火”、“水”、“土”四元。与此同时,西学不承认阴阳是一切现象的根源,只承认阴阳是内在于事物的构成因素。 因接近西学而接受西洋自然科学,接着一接触经验观察及合理逻辑就产生了怀疑儒家阴阳五行说而试图重新解释自然结构的倾向。洪大容反对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天文现象,否定阴阳实体性,认为阴阳因阳光浓淡深浅而异,并非天地间另有阴阳二气。他还认为五行之数不过是术家们的不经之谈,分五星而配为五行也是儒家的胡言乱语。他肯定西学四行说,认天为气,火土为陆地,因为木金产生于太阳及陆地之间,所以同火水土不能并立。 茶山的二哥丁若铨曾经在以五行为主题的策问考试中发表有关四行说的评论文,以第一名及格,但因此而遭到了传统儒家的攻击。茶山丁若镛自己也从来没有承认阴阳五行。他认为“阴阳”是按着阳光或亮或暗而定名的,“五行”只不过万物中的五种东西而已,五行本身不能产生万物。至于理气论,他认为“理”是附属品,有依赖性,没有独立性,从而否定了“理”的实体性。归根结底,丁若镛将西学四元论容纳到“易”的四正卦论的儒家成分上,用来规定新的自然哲学基础。 从以上几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在采用经验性的、证实性的西洋科学的过程中,由于演绎原理的运用而变成抽象理论的传统儒家自然哲学终于为经验主义自然哲学所更替,从而向近代自然哲学接近。 17世纪以后,传入锁国性传统社会——朝鲜社会的西洋科学技术,直到18世纪为一些先进西学徒所接受并消化,既引起了科学的关注,又提高了合理精神的觉醒。与此同时,开始向经验性自然科学接近,从这一点上看来,可以从合理意识中寻找近代思想萌芽意识,而这种合理意识就是从内部克服偏重于“性命义理”并沉浸于道德性、萨满性、巫术性科学知识的朝鲜科学精神。 (三)追求新的人间像:对西教信仰的认识与实践 西学的“理”方面——西教即天主教。从朝鲜王朝后期开始信奉西教,这不仅意味着新的信仰实践,而且还意味着新的伦理性价值体系的接受。性理学的儒学把越出超“天”问题的内在“性”问题当作直接考究对象,对此可以说西学的一面——天主学是人间学的一个方面。由此看来,接受西教就等于其它方面接受基督人间论。如果从这种观点出发,信仰西教的实践便是人的新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生活变革的新人间像的追求。 在来自明清的汉译西学书的内容中,“气”的方面(科学技术)是很生疏隔膜的,但是通过经验可以知道其利器的先进性和有用性。西洋科学知识不仅给儒教性传统科学带来了学问关心,而且为一些先进学者所接受,因而具备了能够克服华夷世界观的条件,也开辟了从先验性儒教宇宙观转变为经验性近代宇宙观的道路。但是,具有先进学问精神的实学者也意识到,只有书学的“理”方面即伦理宗教就会产生不易接近的异质感。因为是通过彻底的注入式教育所取得的学识以及被严肃的常用礼俗几乎硬化为儒教伦理意识的性理学价值体系,所以抱有过分强烈的复辟意识的儒教知识分子就难于接受与此相反的异质性价值体系。 李睟光以后,接近汉译西学书或到北京出入天主堂的学者当中,有些人士关于“西学‘理’方面=西洋的伦理宗教体系=天主教的人间观及信仰生活=天主教的理念世界”的知识情况留下了记载。起初都是简介或简评,后来就有意发表了辟异文献。其第一人为李睟光,直到李承薰才把天主信仰付诸实践,在这180年间所出现的那些记载大都是以传统性理学伦理观为基础的观察,但从李瀷以后18世纪中叶起有一些西学徒开始对西教怀着亲近感和接受意识。对基督教人间观和伦理意识以及宗教生活予以关注,最终付诸实践的中心人物都有李檗和丁若钏、丁若铨、丁若镛三兄弟以及李承薰、李宠亿和权哲身、权日身两兄弟。他们在接触汉译西学书的过程中,对西教予以特别关心,热心阅读西教书,遂由天真庵、走鱼寺讲学会举行集会通过共同讨论会而加强了西教信奉意识。此后,李承薰到北京办理入教正式手续而成为天主教徒,随即回国。李檗等人经他办理入教手续后,从1784年起定期举行宗教集会,遂为今日韩国天主教会奠定了基础。 丁若镛是南人少壮学者之一,早年就信奉西教,发生全国性迫害之后,他呈上《自辟文》,接着同教会断绝了关系。可是,今天我们通过他的庞大遗著可以抽绎其思想内所含有的西教意识。丁若镛与朱子不同,认为“阴阳”本来就没有形体,只有明暗,因而不能成为万物根源。与此同时,他还否认以“阴阳”出现的“太极”或“理”是万物化生的创造力。他举出《诗经》中“唯天生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的词句,借以证明万物的位格的创造主确实存在,认为那就是“天”即“上帝”。认为“天”具有产生人间万事的能力,是主宰世上万事的超越者。在他看来,“天”并不是像朱子的“理”那样的先验性形而上学的存在,而是具备位格的伦理性、宗教性的存在。朱子曾经指出“人虽有气禀之差,但‘理’却相同。”丁若镛反对朱子的这种说法,认为人物天命各不相同,因本然之性互不相同而不能互相“移易”,人有别于物,有灵性、道性等道义之性。 丁若镛把天命分为政治性天命即“得位之命”和“死生祸福之命”,认为“赋性之命”作为伦理性天命,是在人孕胎时产生的天赋的灵命无形体,这就是人乐善、恶恶、好德、耻污的根源。他还认为人心性的天赋道心是“性之好德之命”即“赋性之天命”,行善远恶的道德性努力则是“性之好德之命”顺应“赋性之天命”的伦理行为。另外,他还认为“生死祸福之命”是为上天所制定的宿命性东西。他认为人终究必须按着禀赋(性)进行顺应天命的努力借以分辨善恶,其结果会出现的死生祸福则为天所决定。茶山对东洋性天命的这种认识具有足以同天主思想相结合的可能性。人生来就有“形躯之嗜好”及“灵知之嗜”。说成前者是通过禽兽之性而产生的“人心”,后者则是通过道义之性而产生的“道心”,因而必须以道心节制人心并更加传播道心。认为这样的努力才是修身事天之路。“修身事天”是因内向性修己而通往性之好德之命的“天人际会”的努力,而祭天(周礼之禋祀上帝)则是因外向性祭礼而进行的“事天方法”。丁若镛的这种“事天”逻辑正是通过劝善积功的实践及“未死”祭礼而可以向恭敬天主的天主教信仰过渡的思想基础。 茶山经学是为了摆脱宋儒理气说的学问,目的在于从孔孟经学思想的根本儒学中寻求真儒之“实”。这种茶山经学一方面转变为有神论天观意识,另一方面同他曾接触过的西教书中所获得的天主教理粘在一起,终于从补儒论的立场汇合到信仰实践。 丁若镛把宋儒的“天”意识放在孔孟修身治人的实践儒学以及古经的上天上帝观之上加以研究,从而把“天道”实践潮流——“性理学儒教及传统伦理宗教→传统人间像的追求→现世的义务性实践”转变为“天主学的西学→西教的伦理宗教价值→追求新的人间像→贯通现世与来世的义务性实践”。 李檗同李承薰、权日臣一起被称为创立韩国天主教会的三大础石,遗著有《圣教要旨》,是用韵诗体吟咏西教教理的所谓“天主歌词”。 实学集大成者丁若镛在其流放地康津茶山钻研学问时,每当碰到困难就想念起李檗,可见李檗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丁若镛常常敬佩李檗的经学基础稳如泰山。儒者李檗并不是一读西教书就不假思索地将天主教接受过来并贯彻到实践中去的。他也通过以自己的儒家经学思想为背景的西教书研究而正确地认识到西教,所以才接受了西教。我们从李檗那里可以寻找倾向于近代的实学批判精神。 丁若钟与丁若镛、李檗不同,当辛酉迫害之际,受西教的牵连,以身殉职,遗著有《主教要旨》,是一部可以抽绎早期天主教接受者的西教意识的宝贵资料。丁若钟批判传统天崇拜、自然神信仰、杂鬼奉祀等民俗信仰的理论,虽然非常通俗易懂,但其意识却尖锐而强烈。他在《主教要旨》中,适当地运用身边生活及信仰意识来宣传了他的西教接受精神。丁若钟作为韩国天主教会创立成员及教徒领导人,为不懂汉文的儿童和妇女而拟订韩文教理讲学书,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常备资料以及传统的思考方式,以便易于理解天主,遂有条有理地写出了《主教要旨》。我们可以从丁若钟那里找到合理地追求真实生活的新时代人间像的身影。 综上所述,受星湖学派潮流影响的若干西教实践领导人将天主教接受意识仍然放在传统儒教思想为基础的补儒论立场之上。他们在克服朱子儒家思想方面,原封不动地利用了古儒上帝思想。他们离开程朱理神当为论(原作者用词——译者)而坚信上主上帝是位格的神,接受了天主教的新的信仰体系。 还有值得重视的一点是他们为根除现实弊病而接受了西教。他们认为不仅要通过制度改革、产业振兴、官纪净化等民本政治的方法来改变弊端丛生的现状,而且还要通过新的人间伦理来改造自己的精神结构和实行人间变革,以及去寻找自己永生幸福的方法来解决矛盾。 在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的天主教信仰实践,从狭义上讲,单指新宗教伦理体系的接受,从广义上讲,兼指新价值体系的接受。它虽然在神在秩序内以新的人生观和人生的哲学实践为目的,带有宗教限制,但还是接受了能够克服传统的身份制、职业观、社会规制等的原理。在儒教封建社会里,身份上的尊卑贵贱或职业上的歧视,依据所谓理气的清浊、厚薄、上下等性理原理都被合理化,立足于尊严与平等、爱情与和平等原理的基督教教诲虽然既具有宗教上的意义又把神的秩序当作前提,但确实提出了出乎意外的人间观和社会观。韩国天主教会从创立初期开始就进行了反对班常身份、男女性别、老幼年龄、庶孽出生等方面歧视的教会活动。虽说这种教会活动不过是囿于与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近代精神相差很大的宗教范围之内的,但它毕竟是想要克服传统社会封建伦理及身份矛盾的新的人间像的追求,同时也是新的社会原理的接受。这种“生”的实践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中要寻找真实人生的人间性努力,也是合乎近代思想的向往人间意识及社会意识的历史展示。 如上所述,接变的萌芽并没有直接产生了朝鲜社会的变化,可它是向往未来的思想萌芽,因而受人重视。从精神上可以重新实现接变的历史基础虽然微弱不堪,但在整个朝鲜社会中正徐徐酝酿着。
五 结 语
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发展不仅通过以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为基础的内在的动力来推动,而且还促进民族的智慧。不但如此,它还通过同异质思想、异质文化发生互相作用而展开再创造活动。如果一个民族只顾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在思想文化上就会陷入硬化现象。对这种硬化现象如果无能为力,其民族不仅会丧失崭新的活力,而且在历史发展的旋涡中只能导致没落。要克服硬化现象而推动持续发展就必须有效地利用内外动力,同时不断地对外来文化加以吸收和运用。 17世纪以后,传入传统文化世界——朝鲜王朝后期社会的汉译西学书及西洋科学技术便是施加于朝鲜王国的一种“文化冲击”,是一种“变化的变数”。根据自己的文化意识将中国“西学”介绍到朝鲜社会并加以评论的人都是实学先驱,而且在学问上加以研究的人也是星湖学派或北学论系统的实学者。他们对西学进行研究后,或者作为辟卫论者将排斥西学的逻辑加以系统化,从而先导后世的斥“西教”攘“洋夷”理论,或者埋头于西教实践及西学研究之中。 通过西学学问活动逐渐向近代世界观接近,开始接触合理的实用科学思想而力主接受科学技术,按着西教信仰实践,开始追求立足于尊严与平等原理的新的人间像。西学是通过西洋传教圣徒业已挑选的宗教资料来进行的学问活动,而朝鲜“西学者”的学问精神则是以实学精神为基础的。西学就是批判态度、合理思考、实用挑选等实学性学问阐述。 朝鲜“西学”的学问活动不仅是韩国智性世界对异质文化体系的追求,同时也是实践的学问活动。它决不是异邦人的学问,也不是排挤本民族的学问活动。而且,它既不是无条件的西学附属品,又不是毫不批判的实践行为。 尽管如此,辟卫论迫害势力就依靠“正”与“邪”的死板理论把“理”与“器”混为一谈,致使朝鲜西学遭到强行镇压,甚至疯狂铲除萌发中的朝鲜西学。北学也未能避免暗中镇压,因为北学认识到西学中“器”方面的有用性,所以其进步活动遭到了挫折。与此同时,因为他们把西洋伦理及宗教看做危险要素,所以连当时朝鲜社会迫切需要的西洋科学技术文明都置之度外,致使在西学研究中早已提到议事日程上的近代化萌芽被他们践踏了。 文化上的“外邪”即抵制异质文明和政治上的“锁国”即对外封锁,有必要分别处理,但对此却加以一体化,死抱住辟卫国策不放,以致造成了朝鲜“西学”的桎梏。 虽然如此,为西学者或北学者所觉醒起来的对外开放态度和引进先进技术文明的态度却反映了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趋向。因此,这种近代化萌芽不顾强行镇压和暗中压迫依然在李圭景“名物度数之学”或崔汉绮“运化气之经验哲学”中露出微光而且通过他们的学问而得到持续发展,最终成为开化思想的基础。 被称为欧亚大陆东部隐仙王国的朝鲜王国同西洋文化的接触,并不是19世纪后期开港以后的事情。如上所述,曾经通过中国而进行接触,一些知识分子为好奇心所驱使而接近,一些技术官僚出自职业上的需要也接近过。还曾有过18世纪后期从实学精神上对此进行研究的朝鲜西学的学问活动。通过这样的过程而提高了可能向近代“接变”的思想觉悟,也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实践。 从接触到反应——研究、抵制、接受的演变——然后再向近代化,这样,“接变”的可能性就成长起来了。 朝鲜“西学”毕竟是传统社会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学问,仅仅是一种实践而已。那些西学者并不据有能够改变韩民族历史潮流的有影响力的地位,当时的天主教信仰运动也没有打下群众基础。由于这种脆弱性,有可能使朝鲜向近代过渡的西学,在开花之前,只得遭到不会分辨“理”与“器”的性理学一边倒当权势力的残酷镇压。 由于对这种异质文化、异质价值体系的接触和反应未能采取明智的措施,在近代史潮流中只好落于人后,这一事实让我们只好感到肃然的历史教训,同时让我们回味着把历史引入歧途的那些当权势力的存在。 无论任何时代,都必须积极地接触异质文化体系,而对此主动地加以研究和有选择地加以接受的“接变”的历史性活动则是需要发展的。应该明白,与世隔绝的民族主义封锁态度是回避历史发展的,只能导致停滞与挫折。在奔向地球社会的21世纪行将到来的今天,我们应当重新体会为了民族历史发展的本民族自生的契机。
〔崔凤春 译〕
① 关于欧洲人艺术的简短片语出现在他的著作《小山画谱》卷1,页9,22a—b,转引自喜龙仁《中国绘画》,(O.Siren, Chinese Painting, X,1958,22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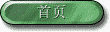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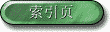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