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佛教史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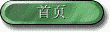




|
四、上座系与大众系在教义上的主要分歧
早期佛教的分裂,直接表现在戒律的宽严上,同时也反映在对教义的不同解释上。对教义的新解释,影响更加深远,往往由此发展成为独具特点的理论体系。这里据《异部宗轮论》等记述,着重从上座系和大众系争论的要点上,考察当时佛教在教理上的某些特点。 1.关于“法”和“法”的争论
“法”,音译达磨,是佛教中概括性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一个范畴。凡有质的规定性,并能引生一定认识的事物和现象,都可称之为“法”。它还有许多特殊用法,如“佛、法、僧”中的“法”,就仅限于佛的说教,是“佛法”的略称。 前已说过,早期佛教最关心的是人生及其解脱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系统见解,主要是通过对“法”的分类,给分类诸法下定义,以及分析诸法间的关系表达出来。作为人生观和解脱观核心的是人(有情、众生),由人的构成上可分解为“五阴”;由人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可分作“十二处”(眼等六根,色等六境);十二处加上主客观作用所引发的六识。扩大为“十八界”。阴、处、界又可概括为“三科”。“三科”中的每一“法”,都给以特定的解释,形成自身的概念,这样,每一概念都蕴含着佛教特定的义理,对诸法关系的分析,也就变成由概念自身组成的理论体系。 但“三科”的范围,其实是包括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一切现象的,固然可以用于对人的分析,也可用来对宇宙的解释。这样人生观很容易扩大为宇宙观;人的解脱问题变成了对世界的解释问题。 因此,关于“法”的问题,成了佛教各派必须讨论的基础问题,分类方法越来越多,概念也越来越复杂。此中引发佛教理论分派最大的问题,是“法”的真假有无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法”的真假有无,是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早期各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体有六种。 (1)“我”、“法”俱“有”论。这里的“有”,既泛指真实不变的存在,也特指佛所说的各种道理。作为“五阴”统一体和业报轮回的主体的“我”,是实在的,作为和合成“人”的各种组成因素和人的善恶等思想行为,如“五阴”等,也是实在的。主张这种学说的有出自上座系的犊子部:出自犊子部的法上部、贤胄部、正量部、密林山部等,也沿袭此说。 (2)“法”有“我”无论。以出自上座系的说一切有部最有代表性,大众系的多闻部也持此论。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包括在“色”与“名”的范围内,它们的本质属性(“法性”)是真实的永恒的存在(“法体”),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都是“实有”。但现实的具体事物,都不是革一的存在,而是由多种“法体”聚合而成,由“因缘”造成,没为自身独立的性质,因而被认为是虚假不实的。“人”就是“五阴”的聚合体,受业报法则的支配,所以也不会有常一自在的“我”存在。这一派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小乘中论著最多、规模最大,以实在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3)“法”无过去未来论。这种主张属大众部本宗义,也为上座中的化地等派别所赞同。他们承认,诸法中的“无为法”,诚如有部所说,是超越时态的“实有”,但“有为法”则否,过去的已灭,没有实体,未来的未生,也没有实体;只有现在的一刹那,才有法体存在,所以说,“过去未来非有实体”。 (4)“俗”妄“真”实论和诸法俱“名”论。大众系伪说出世部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不真实的,属于假名系统。与世俗世界相对的出世间,则非是颠倒,因而是真实的。 传说大众系的一说部进一步认为,不但有为法(世俗世界)是不真实的,无为法(出世间)也是不真实的,它们都是人们给予的名称。 这两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有部的,发展到后来,就形成《成实论》那样系统的宗教哲学;它们的唯名论倾向,是大乘空宗思想的重要来源。 对“法”的有无之争,还有其它一些说法,如上座系的饮光部认为,“若法已断,已遍知则无,未断,未遍知则有;若业果熟则无,业果未熟则有”。这是完全从宗教实践的角度,由行者对“法”的主观感受来确定有无的。 由这些争论看,各个部派对于原始佛理的抽象化和哲学化,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由此形成了两种基本倾向,这就是,上座系各派大都偏重说“有”,大众系各派大都侧重说“空”。说“空”道“有”,成了佛教表达哲学基本问题和人生观、宗教观的主要论题。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佛教的“有”,不等于客观物质的存在,说“有”者,不等于哲学唯物论;“空”不等于否定一切存在,更不等于哲学唯心论。佛教各派对空有涵义的规定,往往有很大的差异,在以后的发展中,也多因为对空有的解释不同,而更新观念,形成新的宗教哲学体系。因此,空有究属什么性质,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言。 2.关于“我”与“无我”之争
“诸法无我”是佛教区别于印度其它教派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联系到业报轮回的宗教教义,便出现了矛盾。围绕解决这一矛盾,各派提出了各种调和的说法,也引起了相互争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制造新奇的名称,曲折地肯定有一个承担世间轮回和出世间惨遭的主体。首先是上座系的犊子部提出“补特伽罗”这一概念。补特伽罗,意译“数取趣”,指可以数数追求人生,数数轮回生死的主体,是全部生命活动的统一体,也是从前世转到后世、从世间转向出世间的联系者,实质上是指与“人”或“有情”形象类似的灵魂,也就是变相的“我”。佛教各派都承认“人”是“五蕴”的和合。犊子部的特别说法是,“补特伽罗”既不可说成即是五蕴,也不可说成是离开五蕴,“即蕴”、“离蕴”均不可定说。这一说法很玄妙,目的在掩饰对“我”的坦率承认。一切有部在理论上坚决批驳有我之说,认为补特伽罗只是一种假名,并不真实。但此派承认有“同随得”,其作用与“我”无本质的差别。经量部针对有部“假名补特伽罗”之说,提出“胜义补特伽罗”,“胜义”是真实的意思。 此外,化地部立有“色”“心”功能的“穷生死蕴”,南传上座部立“有分识”,大众部立“根本识”等,都属”我”的异说。 上述各派提出的各种名称,都是为了完善佛教的基本教义:既坚持“无我”的消极人生观,又肯定业报和修道有积极作用。“我”之由“五蕴”和“名色”的拟人化的规定,更向“心”、“识”的纯精神方向转化。这一转化,伴同“业力”说的更新,正在酝酿一种新的本体论哲学。 3.关于“心性”的净与不净之争
早期佛教把“业”分为身、口、意三种。犊子等部认为,这三业是同等起作用的因素,有部则主张三业统一于“意”,“意”对身、口起支配作用。联系到各派陆续承认有行为的主宰者,而且逐步把这一主宰归结为精神实体,以致关于“心”的本性问题也成了讨论的一个热点。 大众系提出:“心者,自性清净,客尘所污”。意思是说,“心性”本来是清净的,只是受外在于心性的“客尘”(指认识对象)烦恼染污才不洁净的,这就是世间的原因;通过修道,断除烦恼,本净的心性显现出来,这就是解脱。持有这种观点的还有上座系的化地部,南方上座部也有类似观点。 上座系的有部认为,贪瞋痴等根本烦恼,与“心”相应,随心而行,所以“心性”不能说是本净的;但解脱也需依心而行,所以心也有“离染”的一面。“杂染”与“离染”是心的二重性,修道的任务就是去掉杂染心,转成清净心。 以上这些不同的说法,对此后佛教义学的发展,影响都很巨大。 4.关于佛菩萨和阿罗汉的争论
早期佛教文献中的佛陀认为,他的说教是终极真理,他本人是发现真理和传播真理的导师。他的学说应该信奉,他的行为值得效法。他有超人的神通,但他毕竟是人不是神。传说他在弥留之际告诫弟子辈:要依“法”不依“人”。人是有生灭的,“法”才是永恒的。佛教分派之后,围绕佛陀是人还是神这一问题,有过很不同的意见。 相对而言,上座系倾向把佛陀看作是历史人物,认为佛陀的肉体是有限的,寿命有边际。佛陀异于常人之处,主要在于他的思想伟大,精神纯洁高尚,智慧深湛。化地部认为,佛陀仍在僧数,供养现在的僧人比供养死去的佛陀功德还大。法藏部开始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佛虽属僧伽一员,但施佛所获福果大于施僧。据《异部宗轮论》,大众各部普遍地神化佛陀,认为佛陀完全是出世间的,他已经断尽漏失,根绝烦恼。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化有情无不净信。他的肉体、寿命和威力都是无限的。佛陀没有睡梦,回答问题不待思维,一刹那心知一切法,等等。世人见到的佛只是佛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世人以为佛用语言向他说法,事实上佛常在定中,并不言说。佛陀的长相也异于常人,所谓“三十二大人相”,“八十微妙种好”等。总之,从形体到精神,佛陀与一般常人,已很少有共同之处,他被渲染成了神。 与此有关,此时佛教徒对佛陀的生平也开始神化。他们认为,佛之所以成为佛,是他累世修习的结果。佛在前世的修行,称作菩萨行;实践菩萨行的人叫做菩萨。菩萨入胎作白象形,从母右胁出生。菩萨作为佛的准备阶段,也是神异的。 “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略称,意译“觉有情”。大众系推崇菩萨,对整个佛教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因为随着菩萨这个概念的出现,带来许多全新的教义。大众系认为,菩萨已不起欲想,亦无恚怒瞋害之心。“为欲饶益有情”,菩萨自愿生于地狱等恶趣,且“随意能往”。菩萨的这一基本品格,已经孕育着大乘学说的主要点。相反,上座系把佛陀作为历史人物看待,同时提高阿罗汉的地位:佛只有一个或可数的几个,常人修习佛教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阿罗汉标志着人的最后解脱。从最后的解脱说,阿罗汉与佛没有差别。但如前所述,以大天为代表的大众部认为,阿罗汉还有五种局限不可以与佛相比。 总观早期佛教各派的争论,反映了佛教内部为适应社会不同阶层和地区特点的不同需要,从各种外道中吸取营养,促使各自竞相发展的繁荣景象。这一发展,呈现出两种明显的趋势,其一是以大众系为主,向内容日益庞杂的大乘佛教转化;其二是以上座部为主,形成较多地保持早期佛教特色的所谓小乘佛教。这两大系统,在印度的南北,又都各有过不同的经历和风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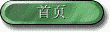




| |